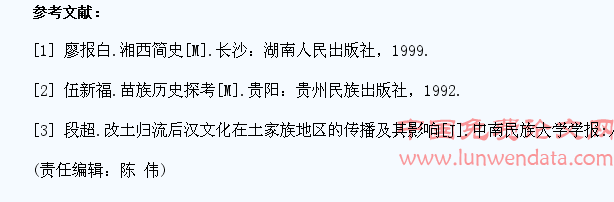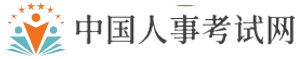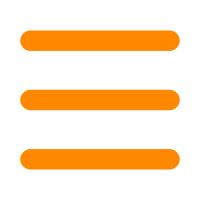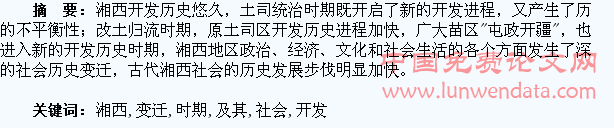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06??0041??05
作者介绍:龙先琼(1963-),男(土家族),湖南保靖人,历史学博士,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1、土司统治时期开发的历史局限
湘西土司规范孕育于五代,形成于宋,滥觞于元,健全于明,沿袭于清初。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彭士愁被授为溪州刺史。后周显德三年,其子彭司裕袭溪州刺史。从此,彭氏世袭土司规范在湘西统治了八百多年。土司规范的实行,湘西地方土司的权力加大了,土司执掌军政大权,改职官为流官担任。这种“土流间用”、“夷汉共活”、“以土为主”的治理格局,既有益于朝廷对湘西的统治,便利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也有益于湘西地方社会的相对稳定。所以,土司时期湘西开发进一步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新的进步。
这一时期,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湘西区域,常见使用牛耕,包谷、高梁、豆类等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开始传入湘西,带动了生产进步。农业耕地面积增加,粮食增多了。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辰州布衣张翘等人联名向宋朝延上书,称“五溪”之地的辰州、锦州、溪州、富州等地“有良田数万顷”(宋史?蛮夷,卷493),觉得可以大力开发。到元代,牛耕已常见用,用筒车提水灌溉农田。耕作方法的进步,可以提升粮食产量。宋代,“五溪”区域产粮较多,但缺少食盐,“蛮人”因此时常骚乱。宋咸平年间,转运使丁谓建议朝廷以食盐向武溪蛮人交换粮食,以提供边防驻军,朝廷采纳。如此,既解决了武溪蛮人的缺盐问题,又使边防军粮有“三年之积”(宋史?蛮夷,卷493)。除此之外,畜牧业和手工业也有新的进步。家禽、家畜饲养类型和数目较多,冶炼业、畜牧业、加工业和纺织业的工艺水平都较高。这类方面的进步,从土司向中央王朝的进贡上反映出来。经济进步了,土司向封建朝廷更多地“纳贡”,以期得到较多“回赐”。从宋到明,纳贡次数渐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品种愈加繁多,马、朱砂、犀角、茶叶、铜鼓、虎皮、麝香、水银、“溪布”等都是“五溪”土司向中央朝廷进贡的特点商品。贸易往来十分活跃,老司城、浦市、王村、里耶、迁陵镇等地成为这一时期的商贸中心。除此之外,统治者比较看重文教事业的进步。元、明两朝采取“恃文教而略武卫”的方案,进步文教,推行文化,规定土司子弟需要学习汉文化。明洪武年间,在永顺打造了书院,施州打造了五卫学(民国《永顺县志》卷21)。明弘治十四年,朝延强令“土司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不入学者,不准承袭”(《明史?湖广土司传》列传198)。一些失意官员隐居“五溪”区域,招徒讲学,传播文化,如南宋时王廷连在泸溪武水口(今五里洲)创办“东洲书院”,办学10余年,传播汉文化;元初,田希吕隐居大庸天门山,创办“天门书院”,传经讲学。如此一来,各地土司程度不同地看重文化教育,也出现了一批文化人,如容美土司田世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宋庆历年间,泸溪的官绅及殷实大户请塾师在家开馆,教育我们的子弟,私塾从此开始在湘西出现。[1](P53)土司时期,湘西区域正式开启了汉化教育的先河。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封建王朝对湘西的治理政策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对于同意土司控制的土家区域和是土司直接统治的“熟苗”区,历代统治者实行的是比较开明的政策,而对于以腊尔山为中心的不为土司控制的“生苗”区则实行高压政策。至“改土归流”,“明、清历代统治者对‘生苗'除大规模军事征讨和镇压外,所实行的政策,总的是以营哨、‘边墙'、堡寨进行军事封锁隔离和借助土司、卫所进行防范、钳制的政策”。[2](P149)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明朝廷耗银数万两,修筑一条从亭子关经镇溪所到喜鹊营的土墙,称为“边疆”,对腊尔山进行封锁。这种政策,阻隔了苗、汉、土家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加深了“生苗”区的封闭性,对“生苗”区的开发和进步极为不利,也加剧了湘西开发与进步中的历史不平衡性。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2、改土归流时期的湘西开发
针对土司规范在沿袭进步中的弊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廷同意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对西南各省土司规范进行改革,取消“蛮不入境,汉不入峒”的禁例,沿袭800多年的湘西土司规范开始全方位废除。至雍正九年(公元1730年),土司统治下各自割据为政、人身奴役紧急、苛捐杂税繁多的社会现象得以改变和禁革,实行统一的流官统治和赋税规范。对于“生苗”区,清廷采取血腥的征剿方法强制推行流官治理,推行对苗疆的“开辟”。
“改土归流”后,湘西土司区和“苗疆”均纳入封建国家版籍,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治理开发政策,使湘西少数民族区域进入了朝廷的比较稳定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有益于湘西区域的局势稳定和经济与社会进步。清统治者采取废弃“边墙”,开放汉、苗、土家结亲之禁,建学宫、办义学,先后开办了乾州厅学、永绥厅学、永顺府学、永顺县学、永顺桂香书院、保靖县学、桑植县学、龙山县学等。学校的打造,起到了传播文化、开启民智的积极推动作用。允许客民入境垦荒,设立集贸市场,在苗族区域推广汉族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如筒车、纺车、养蚕等等,使此后数十年间,湘西社会进一步开发,经济得到较快进步。农业方面,广泛用铁制农具如犁、耙、锄、镰等;牛耕、蜈蚣车(担水工具)渐渐普及,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稻、玉米、红薯、小麦等粮食作物产量不断提升;棉、苎麻、芝麻、油桐、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技术渐渐普及;养殖业也有进步;手工业生产门类扩大,工艺水平不断提升,外地和当地手工业者“彼此相习,艺亦渐精”,“攻木者雕缕刻画,攻金者铸枪炼刀,及所有农器莫不精致坚牢。其他各艺皆日异月新”(民国《永顺县志》卷6)。史书记载当时由沅水、酉水及澧县、沅陵进出湘西的水路、陆路上,商贾络绎不绝,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改土归流”后,“百务咸兴,攻石之工,转植之工,设邑之工,皆远来矣”(民国《永顺县志》卷6)。外来产品不少,“广货川货,四时皆有;京货陕货,亦以时至”(乾隆《永绥厅志》卷2)。湘西的农副土特商品远销全国,“出口货财,日形发达。交通便易,上至川陕滇黔,下至鄂浙闽广,咸有永商踪迹”。原先“稼穑而外,不事商贾”(乾隆《永顺府志》卷6)的土人苗民中,出现了一批商人,其中“妇女居半,苗民尤多”,所贩货物“以谷米为大宗。谷米之属,如豆、麦、杂粮皆有之;畜产之属,如牛、猪、鸡皆有之。除此之外,布帛器用,场期皆随时可售得者”(光绪《古丈坪厅志》卷11)。商人中既有坐商,也有行商。“城乡市铺贸易往来,有自下路装运来者,如棉花、布匹、丝、扣等类,日杂货铺,如香纸、烟、茶、糖等类,日烟铺,亦有专伺当地货物涨跌以为贸易者。如上下装运盐、米、油、布之类,则曰水客。至于当地生产,如桐油、五倍(有羊倍、角倍二样)、碱水、药材各项,则视下路之时价为低昂。”(同治《保靖县志》卷2)商人的贸易水平有了提升,反映当时商业的兴盛。经济进步和商业的兴盛,带动了一批以市场为依托的集镇的兴旺和进步,如龙山的民安镇和里耶镇,永顺的灵溪镇和老司城、王村,保靖的迁陵镇,花垣的花垣镇和吉卫镇(猪市),吉首乾州镇,泸溪的浦市镇,凤凰的阿拉镇(牛市)等,反映湘西开发和进步进入了一个高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傅鼐在“苗区”推行的“苗防屯政”的治理政策在湘西开发史上应该引起足够看重。
在镇压了乾嘉苗民起义后,从总结历代治苗的教训出发,凤凰厅同知傅鼐自觉得“苗区”治理要在武力慑服的基础上,以“化导”为“治苗”之本,以“以苗治苗”为“久安”之策。于是嘉庆四年(1805年),他在湘西“苗区”推行“屯回养勇,设卡防苗”的苗防屯政规范,采取了很多政令手段,如“屯田”制、苗官制,与文教“化导”手段等。“苗疆”屯田,初行于凤凰厅,后始推及乾州厅、保靖县、古丈坪厅(今古丈)、永绥厅。“又因凤凰厅屯勇过多,厅均田不足以养勇,遂再推之于泸溪、麻阳两县。”(《湘西文史资料》,第八辑,第1页)这类政策与手段在一定量上抑制了“苗区”土地兼并的势头,部分调整了“苗区”土地占有关系,使大量“流民”、“降苗”、“苗兵”得以承耕“屯田”,重新回到土地上,成为自耕农,“苗区”社会秩序得以逐步安定,生产进步。这一时期,官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开山修渠,引水灌田,使荒地变成良田。对于贫困农民,官府还借给农具、种子,让其进步生产。农作物品种渐渐从外面传入增多,稻谷、玉米、荞子、红薯广泛种植,小麦也开始在乾州厅推广。粮食产量增多了。史书记载凤凰、乾州、永绥三厅粮价是“三厅米谷甚贱,其他食物俱为实惠”((精)《大清一统志?湖南统部》续编),桐泊、茶油、茶叶、生漆等农副商品的产量也将增长。
1822年,仅永顺县桐油出口就达2万余担,为历史之最。手工业中的纺织业、陶瓷业、造纸业、采矿和冶炼业均有新的进步。民间艺人、匠人的工艺水平较高。土家族、苗族的传统的织布和银器打制技术已相当成熟,商品颇受青睐。农业和手工业的新进步,带来了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此时,“五溪”区域的商路有陆路和水路两种。陆路是由桃源、澧县通保靖、龙山等地;水路以沅水为主,澧水次之。水运货物的集散地分布沅水、澧水的沿岸码头,主要有永顺府的王村、辰州府的浦市、乾州厅的镇溪、龙山县的里耶、保靖县的迁陵镇、永绥厅的茶洞等地。其中,“浦市在康熙年间开始兴盛,嘉庆时有商户数干家,仅客籍会馆达48所”,[1](P131)是当时最为兴盛的商贸中心。同时,苗汉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大,“苗区”文化教育水平有新的提升,“嘉庆、道光将来,湘西苗族各厅县,秀才举人相继辈出,文化教育事业也确实得到前所未有些进步”,[2](P232苗族教育家吴鹤便是其中代表。总之,这一时期的湘西“苗区”开发与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些高度。
3、改土归流后湘西的社会历史变迁特点
从早期的人类活动开始,历程代治理的开发,到清前期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湘西区域的社会历史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改土归流的实行,是古时候湘西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策略性开发举措,对湘西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改土归流之后,古时候湘西社会的历史运行在清前期呈现出与以往历史进程显著不一样的社会历史特点。
(一)改土归流之后,使古时候的湘西社会在清前期开始纳入封建国家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之中,开启了真的的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
自汉开始,中央王朝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政治体制,但对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区域则依旧是承认每个少数民族首领对各自领地的统治,并加封每个首领以王、侯、邑等名号,同时派族官吏作太守、县令,监督各族首领的统治,实质实行的是“附则受而不逆,判则弃而不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卷86)的间接的名义说的政策。中央王朝对包含湘西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羁縻”统治,设置州、县、峒等行政建置,这种行政建置上的中央政府改为使少数民族区域名义上纳入了中央王朝的政治治理下,但事实上各少数民族地方政治具备非常大的独立性,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主要体目前职官称号任免与“朝贡”和“回赐”的礼节性互动上,各州、县、峒等的内部事务依旧按各自规则行事,所谓“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一直蛮夷适之,斯计之得也”(《宋史?蛮夷列传二百五十二》卷493),这就是以蛮治蛮的规范羁縻之制。
羁縻州制下的湘西“蛮酋”权势在唐末五代伴随中央王朝的衰落、分裂而趁机坐大。比如,五代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率蛮兵万余人攻打楚属辰、澧二州,楚王马希范率军反击,双方于次年议和,签订盟约,在“归顺王化”的首要条件下,彭士愁获得更大的权益,尤其是辖区内独立的军权,成为名符其实的“土王”割据统治的独立王国,开始湘西八百年土司统治的先河。土司规范早期,中央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地方“蛮酋”之间由于羁縻州制和松懈而致使的纷争关系得以重新调整,少数民族地方“蛮酋”大姓之间的纠纷争斗也暂时平息,土司统治地区社会政治局面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有益于当地的开发与进步。经宋、元、明几代的历史演进,到明末清初,土司规范的弊病日益突出,朝廷也视为隐患,其“僻在边隅,肆行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清世宗实录》卷64),废除土司规范已是势在必行。
湘西区域的改土归流自清雍正年间开始,至乾隆年间基本结束。改土归流的推行,使湘西区域的土司世袭制被郡县制取代,真的纳入到封建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管理体制中,社会政治秩序得以重构,打造了中央王朝集权下的社会政治新秩序。自此,“土司所属之夷民,即我中国大陆之编氓,土司所辖之头目,即我中国大陆之黎献,民胞物兴,同等看待”(《清世宗实录》卷64)。湘西区域开始真的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原先土司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结束,有益于当地区的各民族的交流和社会政局稳定,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开发与进步,促进了统一的国家历史进程。改土归流后,湘西开发的历史进程加快。
清政府在湘西区域设置府、州、县等政治机构,命流官充任,设永顺府辖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四县,改凤凰直录厅、乾州地隶厅、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校转。以统一的里甲制代替土司的旗长制,改革了社会基层组织;以绿营兵制取代土司旗兵制,使中央统一兵制取代分散割据的土司兵制,以大清律例取代土司家法,确立了统一的法制。同时,实行统一的赋税制,改革文化教育规范。湘西区域开始打造了新的统一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改土归流后,清王朝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生产力得到解放,促进了湘西的经济开发与进步,封建地主制经济得以确立
改土归流后,湘西区域纳入封建国家统一的政治治理体系中,打破了原先土司统治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有益于政治稳定和各民族群众的相互往来交流,为经济所有与进步创造了好条件。同时,清统治者在改土归流中实行一些新的经济政策与手段,促进经济的进步。清政府以统一的编丁纳赋的赋税制取代土司各自为政的赋役制,“或按土户均摊,或照土司征收,旧册摊派,以完秋粮二百八十两之数”,并且“永不加耗”,土司统治时的“所有杂税私征,严行禁革”(民国《永顺县志》卷12)。统一的赋税政策,废除去土司时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多少减轻了各族百姓的负担,有益于民力恢复。对于边远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免除徭役政策,“苗人再经招徕,不征不徭,所以休养生息”(乾隆《永顺厅志》卷3),一定量上保护了边远少数民族的社会劳动力进步。
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中,废除去湘西少数民族区域“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禁令,很多汉民纷纷迁入湘西。据统计,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龙山县人口总数为9.5万余口,其中流民人数3.7万余口,占全县总人数的39.3%[3]。康熙初年,湘西苗区的永绥、凤凰、乾州三厅具备苗寨一千个左右,到乾隆末年增加到四千个左右,人口达3、四十万,其中有不少流民迁入。伴随很多汉人的入迁,汉族区域一流的生产工具、农作物和耕作技术传入到湘西区域,铁制农具、水车、灌田、施肥等工具和耕作技术,与棉花、油菜、油桐等经济作物得到运用、推广和常见种植。同时,改土归流后汉族群众流入湘西,百艺工匠带来了一流的手工业技术,“永顺在土司时自安朴陋,因鲜外人踪迹。自改流后,百务咸兴,于是攻石之工、攻金之工,砖植之工,设色之工,皆自远来矣。”(民国《永顺县志》卷12)工种也渐增多,“土、木、竹、石、裁缝、机匠之属各有专司。”(同治《保靖县志》卷1)手工业较以前有较大进步。清政府还有多种鼓励各族群众垦荒土地,设及土司土地大多数分给农民,实行屯田制。这类政策手段,有益于调动各族群众的垦地耕作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凤凰厅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时,熟田为183公顷7亩,到乾隆年间,就额外丈出和开垦了129顷16亩,面积增加了20%以上(乾隆《湖南通志》卷2)。
经济开发的活跃与进步,促进了商业贸易的进步。土司时期,湘西“邑民鲜逐末,除力田垦山外,别无奇羸可挟,故耕作勤而盖藏亦寡。”改土归流,职员、货物往来交流更为便利,农业、手工业得到进步,湘西的商业贸易日趋活跃,这类水、陆交通要地码头成为商业贸易集镇的如龙山的里耶、永顺的王村、永绥的茶洞和泸溪的浦市等。永绥等地的“鱼、盐、布匹所有食用之物,皆取于中国大陆”,“商人行盐城中”,“列肆者已有其人。”(乾隆《永绥厅志》卷2)一些外来商人十余年间,在湘西“累资巨万,置田庐,缔姻亲”,成为当地“巨族”(嘉庆《龙山县志》卷11),经商者较土司时期渐之增多,财力更大。
伴随经济的进步,很多的耕农出现,土司统治下的封建领主制被封建地主制取代,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那种“土司向例,每用人夫,郡令余把按户派拨,并无夫价,役使无时”(乾隆《永顺府志》卷3)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被实物和货币地租的剥削方法代替,土司时的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得以废除,各族群众的获得人身自由,承担赋税相对减轻,这有益于少数民族区域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湘西社会经济赶上了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经济进步怕整体进程。
(三)改土归流后,清政府推行统一的文化教育政策,古时候湘西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纳入了国家治理的进程,获得了新的历史进步
上司时期,各地土司实行“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文化隔离政策和禁止土司及其子女念书的“愚民”政策,妨碍了各民族文化交流,剥夺了各少数民族群众同意先进文化教育的权力,阻滞了湘西少数民族区域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湘西“建城垣、立学校、开河道、立市镇、置邮传、修祠宇衙署等项……劝耕稼,兴党塾……。均得与被仁义礼乐之化。”(乾隆《永顺府志》卷11)传播汉文明。同时,清政府在湘西区域设立府学、州学、县学等学校教育,兴办义学、书院、家塾等民间教育,开始推行科举考试,汉文化教育渐渐兴起和进步。如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永顺府城建考栅一所,照例岁科两试,府学各取12名,县学各取8名。”(乾隆《永顺府志》卷11)城内上学念书者渐多,“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早自摊磨,亦不以贫废读。”(光绪《龙山县志》卷11)念书者增多,尤其是平民子弟的入学考科,说明教育得到了新的进步。以汉文化教育为主的传入和进步,使古老湘西在改土归流后纳入了封建国家管理的文化教育政策中,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区域文化教育事业的新进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四)改土归流后,伴随新的社会秩序的打造,土司时期的社会陋习被革除,汉族社会生活方法得以传播,古时候湘西的社会生活从此发生了显著的历史变化
从社会生活内容看,清政府依赖政治统治的力量从平时生活的衣、食、住、行、婚姻、娱乐、宗教等每个方面革陋习、禁陈规、施新法,对湘西区域的人民平时生活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比如,改服装,清廷觉得土民男女服装同一不分,实属鄙陋,着令“分别制服”,“服装宜分男女”(乾隆《永顺府志》卷11),倡用汉服;“尔民岁时伏腊,婚丧宴会之际,照汉人服色,男子戴红帽,穿袍褂,着鞋袜。妇人穿长衣,长裙,不许赤足。”(同治《保靖县志》卷11)革风俗,清廷觉得,“欲绥苗民,必先有理苗之人;欲安苗境,须先除扰苗之弊”(乾隆《永顺府志》卷11),如在婚姻风俗上禁土司的“还骨种”、坐床和自由婚配等风俗,强化封建贞节意识;在娱乐风俗上,清廷把土家族摆手舞和苗族的杀牛祭祖当作陋习明令加以禁止。对土民巫术、傩戏、交往、居住等方面传统生活习惯多有限制。清廷的这类手段,使改土归流后湘西社会的平时生活在内容上发生了结构性的整体改变。
从生活方法上看,改土归流后,湘西区域很多汉人流入,土家、苗民受汉文化影响发生变化,出现了生活方法的多元化。加之人身倚赖关系的废除,汉化教育的推行,土家和苗民的自耕农身份确立,新的社会生活主体成长起来,同姓为婚、土司初夜权和一些陋习巫术被革除,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得到进步。传统生活方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土司家族主导的体制社会生活方法让坐落于很多社会性成员多元主体存在的社会主导的封建制生活方法。
除此之外,在社会生活变化程度和水平上看,改土归流后,湘西区域平时生活的变化速度加快,生活事象的新旧交替更多,更自然。如农作物品种,改土归流后玉米、土豆、红薯、哈蜜瓜、莲藕、烟草等传入湘西,水稻种植增加,经济生活更为活跃,平时生活的水平有一定量的改变,说明湘西历史开发的文明进程进一步进步,文化变迁愈加明显。